吴作人的中国画观念分析
由于20世纪的中国处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阶段,主导方向是向西方求取真理,在政治上表现为吸取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和近代科学思想,在艺术上则是学习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式的写实方法(制造幻境和准确地模仿造型的能力)。革命和改良两大激进势力已经在中国占据了清晰和明确的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吴作人对于在艺术上要以写实方法为根本的观念已经非常坚定和执着。
吴作人的绘画观念一方面与上述的绘画观念相关(图画的三个论证[1]),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艺术中也存在的写实绘画传统的延续。由于他追随和拥护徐悲鸿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否定性评价,因此也把改造中国画的任务看成是自己艺术实践的责任和教学的原则,即在观念上强调艺术为人生,艺术切近现实;技术上强调造型准确,画面具有透视、解剖和质感、色彩上的实物感觉。如果以这种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看待、评价和“改良”中国画,即使没有人事、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必然会和持不同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的中国画的继承者(如北京的那些老人)产生冲突[2]。
1957年以后,随着很多的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纠结,吴作人开始了他的中国画艺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透过篆书(“五十以后学篆”)的学习,完全进入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审美价值和不同于西方艺术观念的评价标准(以书法为基础的写意传统),但是受过西方完整训练和深刻教养的吴作人,无法退回到完全、单纯的中国艺术传统中。此后,他的“新中国画”[3]的想法逐步成熟,并且继续用自己的作品来实现。这个“新中国画”的想法,实际上就是用中国书法和写意水墨画中的概括能力来加强和发展再现物象的技术,甚至认为这样的概括能力不仅是必要的(他在1959年主持中央美院第一画室教学期间要求所有学习油画的学生必须学习书法),而且认为中国画在“概括”这种艺术表达技巧上可以超过素描和油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是他对于绘画理解的最高理想境界。至于中国画的表现力问题(即表达的过程可以把艺术家个人的修养和情绪寄托在笔意与墨色中),由于他本人的特殊的文化教养及在诗词和书法上从年轻起就不曾间断的创作实践,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果。虽然他几乎没有强调“笔墨”这个词,但是却已经由另外一条道路接近于传统中国画的境界,从而形成了他七、八十年代独特的,而且是创造性的中国画风格。这种境界即他的“新中国画”的对立面、维护国画传统的艺术家们所强调的境界:“形似最终点莫如照相,照相术发明后,国画何以尚能存在,此证明‘形似’之外有神韵,中画之妙处,即能‘超现实’的神韵精神。”[4]这就是以书法作为审美核心价值的传统国画艺术观念所能达到的境界。
但是,吴作人始终和传统的国画家有所区别。他所选择的中国画道路,与中国画的基本传统轨迹之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到底是以书法的笔法来抒写一个固定的符号,还是以书法的笔法来表达一个物象?由于吴作人走的是(西方意义上的)画家的道路,他把书法最终归结到对绘画的改进之上,以绘画对现实的概括和表现能力作为艺术的最高成就。这里所说的“绘画”,指的是不脱离实景的画面,即illusion[5],画面必须与某个对象和物象的透视、解剖和质感以及色彩上的实物存在相联系。因此,吴作人的中国画创作,与中国传统绘画将画变成为“书”、将作画变成“写”的方法,本质上有差异。
吴作人的中国画贡献
1、吴作人对中国画的研究,反过来对他个人的油画创作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以及中国美协所提倡的(脱离欧洲油画传统的)“中国气派”的油画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油画中由于掺入了诗意的韵味和书法的笔法,从而画出了概括而别有意味的效果,使得中国画的绘画原则和审美理想能够脱出地区的界限,而成为艺术的普世价值。这个工程实际上比一味宣传中国文化的特色对世界具有更广远的影响,这与吴作人先生毕生都在提倡将《文心雕龙》这样的艺术理论著作译成西方文字,让全世界人民共同分享中国艺术理论的普世化成就与贡献的志向完全一致。吴作人之所以能够在油画领域做到融合中国画精华,是因为他在欧洲的学习和进入艺术核心圈子的经历,使他充分掌握了欧洲古典油画的基本技巧与创作能力,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艺术家中还是绝无仅有的范例,因此他所说的“中国气派”,并不是临摹和复制中国古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色彩、构图和造型,(比如董希文就是将油画与年画、敦煌艺术相结合,)而是从绘画的画法层次上进行根本性的突破和挑战,这也是当他在油画技巧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连影响中国后来一代大师的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都对之敬佩不已[6])之后,反而不沿用欧洲习得的地道的欧洲技巧继续作画反而要另辟蹊径的深意之所在。
2、中国画上吴作人的直接贡献是,保持着描述对象的比例上的绝对准确,在用笔时注意对物象的结构和解剖的描写。可以在内在感觉完全熟练地把握对象结构的情况下,尽量利用墨色的干湿浓淡以及流动和偶然性的渗化效果,留下与物象(object)形态上的联络。利用在中国书画传统中笔墨互相之间形成的一气呵成的气韵连动方法,带起主观与客观的一次既受控制、又出乎意外的关联。
吴作人的中国画为什么主要是动物?
吴作人在中国画实践上特别选择动物作为绘画题材,牦牛、骆驼、熊猫等成为了艺术史上具有标识性的图像记忆。
如上所述,吴作人在中国画观念上,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中国画的程式描写和书法写意的境界,而是要通过一次革命和改造,把中国画变成写实绘画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更为概括和有韵味的绘画方法,并且将之看成是促进包括油画在内的人类绘画的一个发展方向。他在油画方面的贡献已逐步为人所认识,而在中国画方面的追求却在今天不容易被人所意识,其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没有选择现实主义艺术观念所侧重的人物画,也没有选择写意传统艺术所偏重的山水画和花鸟画,而是选择了动物画。
吴作人的中国画在题材上主要不是选择山水和花鸟,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回到传统中国画的状态,这是他的老师徐悲鸿和他个人的终生的职志[7],这一点已如上述。(他即使曾经有意向画一些山水,但他的山水实际上是“风景”的概念,是“写生”的概念,是自然实景的再现。这个问题另文别论。)而不选择人物画的原因,却常常难于交待,因为他在人物造型能力和笔墨的概括能力方面极为出色(见图《列宁像》和《少数民族妇女像》)。他没有将中国画的手法主要用来画人物,没有采纳蒋兆和、叶浅予这样的人物国画家的道路,却将如此重要的一次“新中国画”的革命着落在动物上,其原因在于,画人物必须在细节上极为精确,才能画得“像”,才能成其为一张好画,而这个“像”就会把画家的注意力集中于造型的仔细推敲和描摹上,而阻滞笔法诗意的自由发挥,使笔意受到较大的限制,从而不能解决他对艺术的基本理解,即“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最高理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借助其他物象达到。可能是为了与中国传统国画的山水和花鸟题材拉开距离,也为了显现个人的艺术主张和高超的写实能力,在动物身上下功夫就成为他的首要选择。
<<返回
[1] 艺术中绘画的空间都是二维的平面空间,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寻找“平面”的复归,使画成为画本身。实际上画面营造的空间分为三种方式,可定义为1.图画,2.图表,3.书画,只有图表性绘画才能充分的使得画面成为一个平面,而图画,即以模仿真实世界的物体而形成的写实(再现)绘画,是在用各种制造视觉幻觉的效果,来营造三维的虚拟空间。而书画,即以表达人的内在情绪意向而形成的写意(表现)绘画,是在利用符号和形式并超越其承载和象征的意义,来建造一维的心灵的自由。
[2] 徐悲鸿曾于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担任国立北平艺专的前身“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因其艺术主张为北平的传统国画势力所不容,再加上另外一些原因,上任仅3个月后就辞职回到南京中央大学继续任教。1946年徐悲鸿再度回到北平,此次他做好了充分准备,带来了一支教学骨干组成的队伍。然而,接管之初,依然面临着非常艰巨的形势。其学术分歧与徐悲鸿第一次来北平所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徐悲鸿强调写实主义,教学方法基于“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和“直接师法自然”,反对中国画长期以来以临摹为主的方法;而北平的老国画家们则坚持“四王”以来文人画的传统,强调临摹,以山水花鸟为主要表现题材。这种学术上的分歧,直接引发了1947年10月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组三位兼职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因徐悲鸿要求所有国画系学生入学后先学两年素描的规定而罢教,以及之后持续数月的“国画论战”。
[3] 吴作人:“我过去主张只要掌握了造型的基本功夫,再对中国传统绘画工具能熟练运用,就没有问题能‘应物象形’,画出‘推陈出新’的国画来,所以我说:‘我们来点国画’。我自己就练习用毛笔水墨画人物,我说:‘一张不行,两张,再不行三张’,每次我准备糟踏十张纸。所谓‘十张纸斋’,就这么说起来的,至于我所说的‘推陈出新’,只是强调画的表现技巧的新旧,从艺术形式出发。”引自吴作人文革交待材料《关于1953年冬—1955年每周一晚在家里画画的情况》
[4] 1947年10月18日,(与徐悲鸿进行国画论战的对立方)北平美术会董事会在中山公园集合招待记者,此为他们谈及绘画的形神问题的论述。引自《20世纪北京绘画史》第188页第五章“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画坛(1945-1949)”第二节“三位教授罢教事件与中国画发展的论争”(本章内容李树声执笔)(北京画院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第一版)
[5] illusion空间就是或多或少利用人的视错觉及想象能力,模仿和虚构一个写实的空间,这是一切文化中的图画所采取的空间方式,只是手段高低不同,参入的规范有异,在希腊的绘画(以及绘画性雕塑——浮雕)中获得理性的整合,最后在文艺复兴完成线性透视之后获得基本完善,(而它作为一个艺术自觉的独立方式,在西方是十八世纪中期得以完成,从Abrams说)。西方艺术史的基本传统是建立在这样的再现空间的概念上,因为只有这样的空间才能够再现特定时间和特定的现实空间,从而成为对现实存在的一种模仿和记录,由此而成为历史的依据和资料。
[6] 葛维墨:“马克西莫夫看见吴先生在欧洲画的那些画,他很惊讶,画得那么好,他才知道。他问吴先生,现在你为什么不这么画呀?吴先生笑笑没说话。他当然不会理解,吴先生在追求中国民族风格。后来他[吴先生]的《齐白石像》、《三门峡水库》这些画,拿出来的跟他[马克西莫夫]完全不一样,有深厚的底子。所以马克西莫夫在美术学院还是比较拘谨的,他也知道上面有院长吴先生,艾先生是系主任,水平都很高的。所以他到外边去办了一个等于是个班了,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个创作室,在辛寺胡同。辛寺胡同里头很多人跟他画,他在那儿很自由,因为没有顾忌,在那儿他也画了不少画。”(2006年12月14日吴宁采访葛维墨)
[7] 徐悲鸿:“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但常常了事,仍无功效,必须有十分严格之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在二十年前,中国罕能有象物极精之素描家,中国绘画之进步,乃二十年以来之事。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引自《新国画建立之步骤》(1947年,为北平记者招待会书面发言)(《徐悲鸿艺术文集》第5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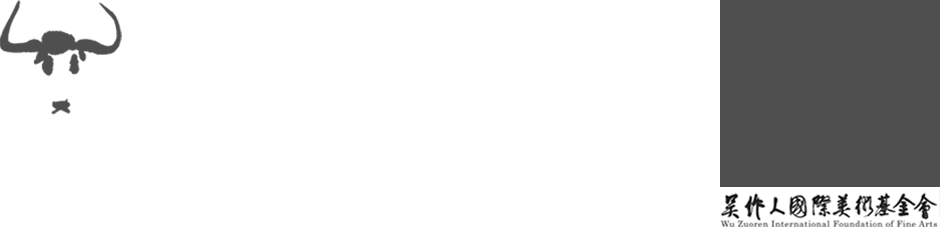
Pingback引用通告: 2010艺术北京经典艺术博览会 |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